2009年春
𝓢𝓹𝓻𝓲𝓷𝓰
喜欢的人是个男孩,这真叫人绝望啊,更别说是校园的风云人物阿尔弗雷德了。一个透明人,暗恋上学院的明日之星,这可真称得上是一部恶俗三流小说的恶俗开头。
当然,我这并不是在刻意隐瞒。
南加州中的部分城市,因LGBT友好开放而著称,无论青少年为玩乐而考取的驾照上明晃晃地标注着的第三性别标记,还是圣地亚哥希尔克雷斯特(南加州著名的彩虹社区核心)每年所举办的规模超10万人的圣地亚哥骄傲节,亦或是法规上明文规定的禁止于就业、住房、公共服务等领域因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产生的歧视,都彰显了这片被阳光终日照射的赐福之地的开放和包容。
但别忘了,越是光明的地方,黑暗反扑起来就越是恐怖。州政府去年通过宪法修正案禁止同性婚姻就向民众释放了这样一个“危险”的信号,而后橙县部分郊区所发生的对学校教材包含LGBTQ+内容的抗议更佐证了这一点:那就是,隐藏在大部分美国人心中的那一份宗教自留地,并不会欢迎这些并不能被耶稣祝福的同性恋们。
更糟糕的是,阿尔弗雷德·F·琼斯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共和党人家庭。其父雷纳德·琼斯早年是个商人,产业在全加州也小有名气,现今则活跃于政界。原先他主张并不受欢迎,但前两年席卷了整个国家的华尔街暴浪意外地成就了他,当前加州民众对于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态度并不明朗,他暴力治安和驱赶非法移民的政见竟然赢得了不少市民的支持。雷纳德·琼斯,一个被时代驱赶上舞台表演的人物,从演讲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Make America Great(让美国更伟大)!”就不难看出他的政治作秀。一向萎靡不振的加州共和党自然拥其为党魁,他甚至成了下一届市长竞选的热门人选。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允许自己的独子爆出同性恋的丑闻?哪怕是沾边,也是毫不可能。
我不敢和金妮透露一星半点的原因也在这里。她向来鼓励我大胆追求,甚至以身作则,报下了她曾经望而却步的AP课程,用来向我证明人的潜力到底可以有多么大!我被那时的她逗得哈哈大笑,她则皱着眉要求我不要再戴眼镜:因为这样会把我那极具东方韵味的眉眼遮住的。想到这,我又忍不住笑了,她就是这样一个大方明艳又极其热烈的女孩,如果我告诉她我暗恋阿尔弗雷德的话,她一定会想办法帮我把这份心意传达的。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互生情愫,想要传递好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哪怕常被人指责太过羞涩和古板的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可问题是,阿尔弗雷德,并不需要我的喜欢,这份暗恋对他而言,必是件沉重的负担。
我不想打扰他,也不想我自己,变成学院里的一个笑话。
今天下午的历史课,是极少数的、所有学生都必须修完的课程,也是唯一一门,我会在课堂上见到阿尔弗的课程。一想到他能在后排看清我的一举一动,我便隐隐有些不安——当然,他可能从未注意到我,我一切的担忧不过是一种自作多情。想到这里,我本应轻松的,但实际上,我的心却更为酸涩了,就像被开水泡过的柠檬皮,皱巴巴的、尝起来也是苦涩的。
“耀…”金妮的胳膊肘轻轻碰了我一下,小声地朝我求救,“什么是Manifest Destiny(昭昭天命/天定命运)?”
我这才回过神来,并不由皱起了眉头。Manifest Destiny,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扩张领土是上帝赐予美国人民的“天命”,希望将其民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从大西洋沿岸传播到太平洋沿岸,甚至整个北美大陆*。金妮的历史很一般,但我却很擅长这些,因此,我更嗅到了这一“教学任务”的敏感:这种思想,充斥着种族与文化优越性,即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优于美洲原住民、墨西哥人和其他任何非欧洲裔群体,有责任“教化”或取代这些人群*。一般而言,加利福尼亚的教材对此呈批评态度,并指责其为“毫无人道主义的掠夺”,但市长选举在即,不少人同意雷纳德的暴力治安以及更强硬的遣返移民政策,而这几乎会是曾经“血泪之路”的再现。想到这里,我不由回头看了阿尔弗雷德一眼,却又发现,同样有不少人的目光,灼灼地聚集在他身上。看来,远不止我一个人想到了这些。
Mr.Willion 清了清嗓子,向整个阶梯教室里的学生问:“Manifest Destiny是扩张的理由亦或是借口?有谁能告诉我你自己的观点。”
“emmm…没有人举手回答,我就点名了——”
“王耀。”
我站起来,带着一种几乎是冲昏头的愤怒,一字一句地拼出了这个单词:“Settler Colonialism(定居者殖民主义),这是一种定居者殖民主义,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扩张借口。”
我说得很准确,这本就是加州的教科书所应持有的微妙情感色彩。Patrick Wolfe学者曾提出: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以土地为中心的结构性暴力”*。我初读到这里的时候便非常赞同,但这种说法还不足以消解我对这种事件的恐惧,一个中国人在他的书中所提到过的一段话更接近我的观感,概括起来是相当血淋淋的四个字——
亡国灭种。
不仅将“敌人”驱赶出土地,还要斩断“敌人”的文脉,降下虚假的、伪善的“教化”。
并将其称之为——“天命”。
他并不评价我,只挥手示意我坐下。
“Ethan Miller(伊森·米勒),你呢?”
伊森站起来,他并不喜欢历史课,但如果能拆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亚裔的台的话,他不介意开口:“先生,我觉得前面的那个同学可能并不太了解美国史,”他裂开嘴大笑,“毕竟America is America for Americans(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我们把民主制度带给其他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这简直是耶稣转世。”
他依旧不评价,只是让伊森·米勒先坐下。
“哦,现在有人举手,金妮,你怎么想?”
金妮咬着唇:“Mr.Willion,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问出这个问题?我们的教科书不是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吗?While it was framed as a divine mission to spread democracy and civilization, it often resulted in the displacement and suffering of Native American tribes and…(尽管它被描述为传播民主和文明的神圣使命,但它往往导致原住民部落的流离失所和痛苦,以及…)*”
威廉老师打断了她。
“金妮,感谢你的分享,我当然知道书上有对应内容,但我需要知道大家的想法。”
我的眼眶湿润了,金妮,你不必为我做到这个程度…
“Chad(查德),可以给我点你的意见吗?”
我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一个被霸凌过的可怜鬼,只因他肥胖的体型不能般配这个极具优越感的名字,以伊森为首的一群人常常喊他“Chubby Chad(胖Chad)”,金妮讨厌这样,她骂跑过他们。
查德颤巍巍地站起来:“嗯…嗯…我觉得伊森说得有道理…”
金妮在底下愤愤不平:“这个胆小鬼!亏我之前还帮过他,现在,让他跟他们那一群人下地狱去吧!没主见的胆小鬼!鼻涕虫!”
Mr.Willion继续打开他的花名册,但我认为他是早有预谋,果然,他那张薄唇里吐出一个名字,犹如点燃了萨拉热窝的导火索。
“阿尔弗雷德,可以说说你的看法吗?”
我不敢扭过头去看他,我惧怕听到他的回答——一个残酷的、却符合他身份的回答。
阿尔弗站起来,他的金发犹如点燃了太阳,永远耀眼,永远绽放着光芒。所有人都在等待他的回答,
“阿尔弗?”
教室里一片死寂,Mr.Willion的声音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回响,我听见它如同一个幽灵一般,飘荡在这个每个人都没有、也不能连接着的孤岛宇宙中。民主是一个谎言,它像一群美丽泡沫,充斥在这个国度的方方面面,阳光透过它的畸形曲面,反射出更加光怪陆离的光线,也同时创作出一个更光怪陆离的世界。某一个瞬间,我几乎是想扔下笔,踩在那颜色沉寂的桌面上,大喊大叫。距今二十年前,一部名叫《死亡诗社》的电影被搬上屏幕,拯救了那些在整个夏日终日无所事事的青少年们,而我现今的出格行为会把阿尔弗从这种难堪里拯救出来,只要我谎称自己正在模仿唐吉诃德就好。我将会说,我将会说:
“O Captain! My Captain!*”
阿尔弗站·F·琼斯站在那里,始终一言不发。
“阿尔弗,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Mr.Willion,我没什么可说的。”他昂着头,那深蓝色的瞳仁倾斜,其中倒映出那永不消逝的泡沫:“我是无神论者,我并不相信什么天命。”
他在说谎。
我在椅子上坐立不安,细细咀嚼着他仅留给我、也留给这一整个宇宙的神谕。然而,我又一次确信,他在说谎:他从未见过真正在无神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他决不能想象——造物主残酷地把人类和地球赤身裸体地放置在天风大浪中磋磨,但不会有任何神明相助*。阿尔弗雷德·F·琼斯,自身相信天命,这种天命既是对他人的拯救,也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浪漫;他自命不凡,认为自己便是那个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挥着米字旗便能解决一切异变的开端。可倘若降下的天命异化成另一群人的天灾呢?否认这种“天命”,灾难难道就会撤散了吗?
“是吗?阿尔弗…”Mr.Willion露出了他今天的第一个微笑,但却绝称不上友善:“真有意思,真有意思…真的…我说真的…”他止不住地拍手,然后又转身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奋笔疾书。
“A.M.E.R.I…”我一字一句地念出来。
“A”如灯塔,沉默耸立;”M”是双拱门,左右皆可通行人;”E”似山倒,只见颓势;”R”如人叉腰又伸腿,东倒西斜;”I”直脊静默,恰似一棵枯树苦苦支撑;”C”是一个围了一半的圈,人不愿见其未完;”A”再次出现,如衔尾蛇般头尾相连。
A.M.E.R.I.C.A。
Willion近乎疯狂地在黑板上书写,粉尘四溢,惹起前排的一阵捂鼻。他字写得极大,熟悉的字母甚至因为过度的巨大化令观看者感到眩晕,迫切想要呕吐。
AMERICA。
这七个字母蔓延。
人群中弥漫一种恐惧的情绪,他在写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的疑问遗留在很多人的心间,却无人能够解答。
叮铃铃铃铃铃…
“下课。”铃音响了,从壁画上走下的犹大也该回到他应该待着的墙面。Mr.Willion如梦初醒般,他碾断握在手心里的那节短粉笔,又重复一遍:“下课。”
我再次盯着他那湛蓝的漂亮眼睛。
阿尔弗雷德,你为何沉默、又为何三缄其口呢?
我不明白他的沉默,一如我并不明白,我为自己寻找的,那个喜欢上他的拙劣借口。
我想起了我喜欢这个男孩的理由。
那是去年春天的一个午后,我为了躲避阳光来到校图书馆,金妮对此避之不及。“王耀!你为何总喜欢出入这种场所呢?”她不满地嘟囔道。我宽容地笑笑,原谅了她的无理:“大概因为我是吸血鬼,就喜欢待在这种充满灰尘的古老地方吧。”金妮撅着嘴甜腻腻地撒娇(当然,她在人前还是好端端的一副女王做派):“我可不想去这种地方!不过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生物实验报告借我copy一下的话,我也不介意陪你。”
我觉得好笑:“当然可以啦金妮小姐,只要你不要一板一眼地全部照抄上去就好了。上次Lily女士质问我,为什么我们的数学解答过程会一模一样时,我可出了一把冷汗!”过了一会儿,我看她无所适从的样子,又心知肚明地对这个好女孩说:“快别陪我了,我知道,南海岸广场的折扣日比我更需要你。”
她眼睛亮起来,神色夸张地给我抛了一个飞吻:“我就知道,耀你最好了!”
就这样,我一个人踏上了图书馆的探险之旅。
我喜欢待在这里,无论是昏暗的灯光、浮动的灰尘还是油墨的味道,都令我安心。在一排又一排的书架之间,我故作闲庭漫步之态,像一个帝王在环顾他的江山。首先是走向文学区,匆匆挑选了几本通俗读物,别问我为什么不多读些高雅的!日常活着已经够累了,当然需要一些轻松读物来缓解一下疲惫的心灵。接着又奔向自然科学类,我答应了金妮会把实验报告交给她,在这个承诺的基础上,我决心把这份报告做得更好、更出色,这样也好给怀特老师一个交代。
事情是这样的。
怀特老师在课堂上咬着牙吼叫:“伦理审查组的老古董可真是可恶!我和他争执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申请通过了血液携氧能力的实验。兔崽子们!听到了吗,给我好好地用鱼的血液和牛的血液来进行对比!看看鱼类和哺乳动物到底有什么不同!”
血液,这可真可怕。我小心翼翼地用移液器收集到了一点离心后的“实验材料”,并将其放置在我的载玻片上,打算仔细观察。
“王耀王耀!”查德小声向我求助,“你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看到。”我悄悄做了个鬼脸,骗他。
他神经衰弱地絮絮叨叨:“哦!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做这种实验有什么用呢?它们只让我想要——呕吐!”说罢,他安静了两秒,又重新用一种故意挤出来的、阴森森的语气说:“你知道吗?怀特老师私底下,想要说服学校,用人血来教我们做实验!”
我吓了一跳,“人血?你是说,真正的人类血液吗?”
查德非常满意我的反应,并进一步凑过来:“当然了!但学校以成本过高和伦理道德问题拒绝了他!你知道吗…他还说…他还说…”
“他说了什么?”
“他还说:加州贫民窟的血浆站比天上的星星还多,随便去买几袋不就好了吗…”
我没能听清楚他后面的话,因为怀特老师冲我们大喊:“查德!王耀!你们在交头接耳地说什么呢?你们两个人,实验报告比别人多写一千字交给我!”
事情就是这样。
我口中不自觉地念着:“Blood、Blood、Bloo——od…”一边用我的指尖,轻轻摩擦过整齐排列好的书脊,它们如海浪般轻轻晃动,我则想象自己是一只永远不能在海面上停留的海鸥,哦,就如同我怀里的《荆棘鸟》一般,一生只找到一棵荆棘树栖身,把刺扎进了胸口,然后放声歌唱,那歌喉竟比云雀还美。我不由自主地念出了书中的原文:“Because the best things that can only be painful huge hit in exchange for.(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
“噗——”
我听见一声轻笑,像蘑菇云一样炸在耳边。我几乎要惊得跳起来。
“谁在那里?”我用隐秘如尘埃的气音问。
图书馆里静悄悄的。
我屏气凝神,企图找到这一点声音的来源。
“谁在——谁在那里?”
没有人。
窗外阳光透过大片玻璃窗照进,灰尘飞舞在光线下清晰可见。我抬起手,妄图触碰和我近在咫尺的光芒,接着又赶紧将手指收回。窗外树叶传来沙沙的风声,图书馆的团宠三花猫咪吉利一跃而过,我疑心这正是它发出的动静…我疑心是我刚刚幻听。
我终于不再玩乐,而是真正把书抽出,一边抽还一边念出它那烫银的名字,甚至越念越快:
“*Blood: An Epic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Commerce*”
《血液的故事》
“*Williams Hematology*”
《威廉姆斯血液学》
“*Basic Hematology*”
《基础血液学》
我猛地抽出最后一本书,就连心脏也激烈地跳动,以至于后来的我分不清这时的心跳是紧张兴奋,亦或是什么别的东西。
而当时的我只想着:
抓到你了!
抽出书的空隙,时间也在此悄悄停滞。我借着这一点点透光的空隙,嗅到了暮春的花粉气息。
我看见,我看见——
我看见一只蓝眼睛。
刚刚出现在我幻想里的大海突然实体化,那中间的深色瞳仁就仿佛伫立于海浪中间的岛屿,用来供以某一只海鸥的栖息。那鸟儿不由分说地振翅,羽翼遮盖小部分天空,只将振落的羽毛遗留给大陆。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
阿尔弗雷德也被我吓了一跳,他把刚刚抽进书架的那本书放稳,便匆匆逃离了图书馆。我看见被书架遮盖了大半的他的背影,什么也说不出口。他甚至没有像灰姑娘一般留下水晶鞋,没有给我留下可以与他相遇的信物。
我轻轻地叹息一声,转过书架,去找他遗落在架子上的书籍,上面还残留着他尚且温热的指纹,我眷恋地摩擦过美丽烫好银的书脊,一下将其抽出。
奇怪…这里面好像夹了什么东西…我好奇地翻开,只见里面夹着一张小卡纸。图书馆近来冒出个神秘传闻,说是有黑衣人士偷偷往书本中塞上卡片,上面尽是些和学校教育截然不同的胡言乱语,是用来毁坏加州的教育的。谈论这些的人说得十分隐秘,我也并不能如桃金娘一般窥探到他们讲话的全貌,以至于连这秘闻中卡片的实物也是从未见过。难道?这就是那秘闻中的卡片吗?我掌心泌出汗来,小心翻开这“潘多拉的魔盒”,只见卡片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加州血浆产业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剥削,以每周两次、每次50美元的报酬来获取廉价血液,并将这些血液高价出口。上面的小字一行一行触目惊心,完全不同于以往学校和社会所宣扬的“献血拯救他人”的口号。我一时怔在原地。
我知道的,我的有些同学,会依靠卖血,来赚取自己那高昂的学费。但这件事离我太过遥远了,我总是刻意不去想它们。
查德那叽叽喳喳的厚嘴唇在我的眼前翻转:…加州贫民窟的血浆站比天上的星星还多,随便去买几袋不就好了吗…
实验室里的血液,好像突然是从我的血管里抽出来般、一点点离开我的身体,我一阵干呕,脱力到仿佛不能站起。生命的实体,仿佛在我的灵魂中流失,它并不和我分别,便要自顾自地走入长夜。我只能如同一艇被失控洋流卷起的小舟,迫切地想要抓住些什么,证明自己不会随风一般流去。紧紧握着的那张卡片,近乎在掌心中留出血痕。
这张卡片,会是阿尔弗雷德放置的吗?
他在其中,又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男孩留给我的疑问太多,他连同春日的温柔和残忍,在我的心中一起扎根。
从那一天起,我不自觉地开始关注他,会一遍又一遍地用鹅毛笔蘸着墨水在纸上写下他的名字,然后迅速划去。某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我困倦地在刚下发的书籍上签下我的姓名,然而笔一连,又无比丝滑地流淌下“阿尔弗雷德·F·琼斯”。它们并排在一起,看上去无比契合,心中突然有一道惊雷把我惊醒,我握着笔,讲台上面的玛格丽特女士正在念诗: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
(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这诗将长存,并赐予你生命。)
那时候我看向窗外,云雀叫了一整天。
“耀!耀!你怎么呆住了呀?”金妮嗔怪道:“你不是想去辩论社看看吗?这可是他们这学年最后一次招新。”
“哦哦。”我这才回过神,想要踏上台阶,跟上金妮的脚步。
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抱歉,我想问,你们也是去参加辩论社的招新吗?”阿尔弗雷德手插在兜里,我不明白他是故意要在金妮面前装酷还是什么?他刻意咬着一点尾音:“或许我们可以一起。”
唉…他都摆出了如此姿态了,难道我们还能拒绝吗?
金妮挤出个笑:“当然可以。”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氛围或许有些尴尬。金妮装作无事发生,实际上她拿出手机猛戳,朝我发送了一条又一条信息。
“我都能想象这花孔雀来了之后有多少笨女孩们趋之若鹜了[微笑][微笑]。”
我背着手走,将面前的小石子踢了一下又一下,心里温吞吞地说:
金妮,我想,或许我也是“她们”中的某一个?这可真说不准呢。
*周更7500+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告诉我吧^^
下周三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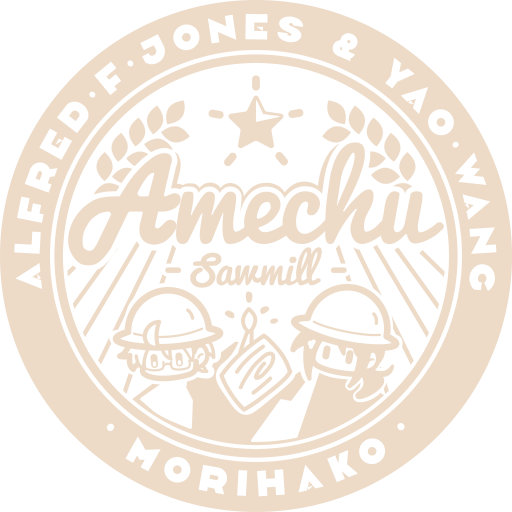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