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题作者:樱桃白兰地
—————————————————————————————————————————————————————————————————
密 封 线
出题人建议:不完整的大纲题目,在原定框架上对故事进行撰写,切入故事时间点不限,要求内容包含大纲内容,可以基于大纲对故事进行扩写补充。
正文答题处:
阿尔弗雷德跟表哥第一次出海,是在十六岁的夏天。亚瑟常年在海上经商,两三年才回来一次,给他讲过许多关于远海和岛屿的故事。
可直到他跟亚瑟登上船他才意识到,他那风光霁月的表哥根本不是什么商人,而是刀刃舔血的海盗。
阿尔弗雷德坐在床舱的房间里,看着狭窄舷窗外被一小块风光照亮的起伏海面,海水拍打在船身上发出令人不安的声响——他上船已经两年了,和这艘船深深绑在了一起。
甲板上能听到海盗们的谈笑声,他们大声唱着歌,酒水的香味从头上渗下来,诱得阿尔弗雷德不自觉舔了舔干裂起皮的嘴唇。他珍重地合上桌边的小羊皮笔记本塞在怀里,推开椅子想到甲板上去参与这场盛宴。变故就在此刻到来。
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响彻整个船舱,一切的欢庆都被打断,奔跑的脚步声开始在甲板上乱砸。
在一片混乱的叫喊中,阿尔弗雷德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的船触礁了。
该死。
说实话,触礁导致沉船的概率很低,日日与死神作伴的海盗们所拥有的船也必然不是一碰就碎的花架子,只是这样一来靠岸的日子必将延期,而他与新鲜水果、蔬菜,贩卖贝壳与海螺的小贩,与陆地的距离,便会更加遥远。
十六岁的少年依然有着向往冒险与宝藏的心,但野花与拂过树林的微风才是占据了他大半人生的那部分。若能靠岸,几乎所有海盗都会涌向酒馆或是红灯区,只有阿尔弗雷德悄悄离开,找一片长满野草的山坡,双手交叠在脑后躺着,轻哼着儿时的歌谣看月亮。到了后半夜,醉醺醺或是假装醉醺醺的亚瑟会找到他,笑话他果然是个男孩而非男人。“去你的。”两年的时间足够让阿尔弗雷德无视这种玩笑,真正重要的事是趁着这段短暂的陆地时间做好补给,蔬菜与水果很难储存太久,上岸的海盗们便个个都像饿久了的猴子似的把水果摊扫荡一空。也多亏了亚瑟定时靠岸的英明决策,处于发育期的阿尔弗雷德才得以营养均衡,加上在海上的风吹日晒和先天优越的脸庞,显出一副健美的模样。
阿尔弗雷德没有行动,他相信海盗们处理危机的能力,便也心安理得地行使了海盗头子的表弟的小小特权来偷懒。但刺耳的木板碎裂声随即响起,他变了脸色向甲板冲去。光线的急剧变化令他有些头晕,等缓过来站稳时他却不由得愣住了——
面前这块近乎是小山般不容忽视的礁石,经验丰富的海盗们怎么可能傻乎乎地撞上去?
没时间细想,众人乱作一团,拼命带上家当。阿尔弗雷德静静地站在混乱边缘,哪怕知道自己和他们身处同等险境,却有一种奇异的平静,仿佛那些愤怒或绝望的大吼是从遥远的天边传来的风声。他不想死,也许他才是整艘船上最怕死的人,但他也知道此时越冷静,才有越大的概率活下去。几个入伙不久的新人冲向他的方向,惊恐地嚷嚷着应该马上修补船侧的窟窿。“笨水母!”有人嗤笑了一声。阿尔弗雷德回过头,亚瑟手插着裤兜站在他身旁,粗粗的眉毛拧成麻绳似的一股。他没接腔,只沉默地接过亚瑟递过来的水囊和干粮,毕竟但凡有过一段航海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这艘船已经无可救药了。更何况他们身处大西洋的核心海域,地图上数百海里内连一座岛屿都没有,如同水构成的撒哈拉沙漠。
“阿尔。”亚瑟出声,沉沉地叫了他一声。他抬起头,望着表哥狼一样的绿眼睛,头一次从其中感受到歉疚的情绪。亚瑟嘴张了半天,闷闷的憋出一句:“你不会死的,祝你好运。到时候在家乡集合。”
好运?希望待会能分到块比较大的船板。阿尔弗雷德扯了扯嘴角,想道。
他低头把必需品塞进背囊,再抬头的瞬间,世界仿佛沉默着静止了一霎,随即船体发出更为尖锐的哀鸣。这是为海盗们奏响的丧钟。
大浪淹没他的那瞬间,阿尔弗雷德紧抱着船板海水里翻滚,他本能地上浮,虽然提前闭紧了气,但是海水还是在翻滚中不可避免地灌进了阿尔弗雷的呼吸道里,留下一片火辣辣的呛,他抠死了手里唯一一块浮木,在海浪中努力调整着姿势,但是却不幸被一块较大的船只残骸猛撞了一下,身体不受控地被卷进巨浪里。
从被亚瑟骗上船开始,他就预料自己大概率有一天会死在海上,他不算太喜欢做这种流血的买卖,但他也放不下这种被冒险和财富包围的生活。大概是这种贪心触怒了上帝,让他早早地遭到了报应,他要死了。
模糊中,他似乎看到漆黑海面翻涌之间,有什么巨大的物体破浪而出,月光下,它身上的鳞片泛着奇异的光泽,硕大的身体朝着海面重重砸下,不知是否是他的错觉,它巨大的头颅似乎向着他这边偏了偏,阿尔弗雷德还没来得及去细究,就被巨浪拍得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是正午,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身上,阿尔弗雷德是被渴醒的,伴随着意识的苏醒,随之而来的是全身泛起的钝痛。
他恍惚意识到,他没有死。
他尝试着动了动手指,换来的是一阵钻心的疼痛,倒吸一口冷气时却发现自己发出老旧风箱般的气声。多次尝试后,除了为数不多的体力被再次耗尽以外,没有任何进展。阿尔弗雷德索性不再挣扎,想象自己是一只即将干晒死的海星。阳光毫不避讳地洒在沙滩上,模模糊糊镀上了一层金色,仿佛所有海上冒险家心目中的黄金之国,遥远而永恒的东方天堂。
阿尔弗雷德闭上眼睛,久违地做起了祷告。
等他再醒来时,太阳依旧毒辣,似乎是没过多久。遗憾的是这次他的体力并未恢复太多,而随时间流逝而增加的饥渴感更是加剧了他浑身的疼痛。不能在这里等死,他想。他磨蹭着沙地,用尽全力向不远处的树荫爬去,身后留下一段蜿蜒的痕迹。
光线的颜色逐渐变化,阿尔弗雷德知道现在已经快到日落时分了。若是往常,他一定会坐在舷窗边静静地看夕阳,手边放着精致的墨水瓶、羽毛笔、以及他最珍视的小羊皮笔记本。
可现在,夕阳和未来都在他看不见的背后,他的前方只有那一小片树影。
太阳已然落下,黑夜同着海浪向阿尔弗雷德席卷过来。
//(略显凌乱的字体)。
这是我困在岛上的第一天,船的碎片漂过来,没带来那些维持生命的物资,却奇迹般地送来了几乎完好无损的墨水瓶和笔。感谢上帝,我可以继续写日记了。
也许是我的祷告起了作用,上帝派来天使把我从地狱中拉起。我几乎一整天都意识模糊,凌晨时的露珠从树叶上滴下,我的嘴便靠近它们,使我得以活下去。傍晚前我的意识稍加清醒,于是看到了我这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夕阳,以及从夕阳中向我走来的,上帝的使者般美丽的,东方面孔的男人。//
阿尔弗雷德以一个狼狈的姿势趴在沙滩上,身后蜿蜒着一道夹杂了血迹的爬行痕迹。至少弄条鱼吃。他忍受着钻心的疼痛用手臂撑起身体,向海边挪去。
夕阳刺得阿尔弗雷德眼前发黑,等缓过来他才发现站在一旁的男人。男人墨色的长发被一根红绳松散地扎起,琥珀金的眸子疑惑地定格在阿尔弗雷德脸上,思忖了半晌,男人转身消失在影影绰绰的树丛中。不久后男人返回,用巨大的叶子包裹着几条新鲜的海鱼,宽大而奇特的衣衫被风吹起在身后,衣摆上的暗纹隐约透出金色的光泽。
“你是谁?”
阿尔弗雷德开口时才发现自己的嗓音早因干渴而沙哑的不像话,见男人不说话,便索性不再开口。也许是附近的渔民吧,他这样想着,拿了条沙丁鱼在海水里涮涮,不经烹饪便咬上了脊背。鱼肉味道微微有些发甜,不过对他来说味道并不重要,补充体力才是第一要务。待他狼吞虎咽完毕才想起来那个男人的存在。可当他回过头时,身侧早已空无一人。
//(草草写下的字迹)
第二天,建了海边的临时庇护所。那个男人又来了,带了足够多的鱼。食物问题总算不用担心了。不过,他是从哪来的呢?
……
我偷偷跟着他想找到离开岛的方法,居然莫名其妙跟丢了。真是奇怪,理论上这附近并不是东方,怎么会出现他这样美丽的东方人?他来自哪里?//
//(划破纸张的笔迹)
第四天,我产生幻觉了?是食物中毒吗?那绝对不是纹身!他行走时衣摆会飘起来露出优美的脚踝,但那些覆盖在皮肤上的暗金色鳞片……不,我绝对没看错……也许是一种装饰吧?也可能是某种古怪的皮肤炎症,不过我从未听过人身上会长出蛇一样的鳞片//
这是阿尔弗雷德困在岛上的第七天,大概是因为语言不通,那个穿着奇异服装的男人依旧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他总能在每天傍晚太阳落山前准时出现在海岸上,给他带来一些新鲜的海鱼,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做。
阿尔弗雷德实在好奇:他是从哪来的?他猜想这个男人大概是附近住在附近岛屿上的人,每天会出海打鱼,顺带给他带一份食物,但阿尔弗雷德从来没亲眼看到他上岛或离岛,也没找到过他的渔船。
这天他又来了,这次他不仅带来了海鱼,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感谢上帝,阿尔弗雷德已经不知道多久没吃到过新鲜的蔬菜水果了。他激动得跳起来,由于语言不通,他只能通过拥抱表达自己的感谢,男人明显不适应这种过度的热情,不自然地缩了一下,后面想到什么,还是让他抱了。
阿尔弗雷德手脚并用地邀请男人留下来陪他吃一顿晚饭,这不能怪他,他实在是太想离开这里了。他知道有些岛上聚居地非常排斥外来者,他也不强求上岛,但他也确实非常想向他们索要一只可以出海的船,让他可以离开这个荒岛。
男人看着他手脚并用地比划,挑了挑眉,这让阿尔弗雷德很怀疑他那个眼神是不是在看傻子。但在离岛欲望的驱使下,阿尔弗雷德怕他没看懂,还是硬着头皮比划着。过了许久,男人嗤笑一声,走到他搭的营火旁边坐下,从身上不知什么地方掏出一把小刀,熟练地处理起食材。
阿尔弗雷德见他接受了邀请,呼出一口气,也靠过来坐下。
处理好鱼,男人又从衣服里掏出几个小罐子,大概是什么调料,一通操作下,烤鱼很快就散发香气。好几顿都草草解决的阿尔弗雷德瞬间瞪大了眼睛。
给他烤完鱼,男人只是看着阿尔弗雷德吃得香,自己却没有吃,只是拿了个果子靠在边上啃,神情悠然得好像这座岛是他家一样。
大快朵颐之后,阿尔弗雷德心满意足地抹了抹嘴,转向男人。他比划出一条船的形状,又指了指大海。男人又露出嫌弃的表情,转过半边身子,神情惬意地欣赏着渐渐落下的夕阳。待四周模模糊糊涌上黑暗时,男人起身抚平了衣衫,准备离去。
“Hey——”阿尔弗雷德眼看着两人的交流毫无进展,情急之下伸手攥住了男人的袖子。指尖不慎划过男人的手腕时,阿尔弗雷德被冰得一激灵。好冷,就像他落水那天的海一样冷。
男人停住脚步,抬眼看着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对上那双暗金色的眼睛一时有些失神,男人略微竖起的瞳孔像是某种美丽强大而又危险的东西,令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沉默了半晌,阿尔弗雷德指了指自己:“阿尔弗雷德。”他多日不开口,有些艰涩而缓慢地念出自己的名字,“阿尔弗雷德-f-琼斯。”男人看了他一会,眼中情绪复杂,半晌学着阿尔弗雷德的样子,拢起宽松的袖子指了指自己:“王……耀。”他发声仿佛比阿尔弗雷德更为困难,两个音节之间有漫长的停顿。“WangYao?”阿尔弗雷德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再抬头时,王耀已不见踪影。
次日上午,阿尔弗雷德在岛上闲逛,在岛屿的另一边发现了熟悉的船只的残骸。他想着也许还能翻到些许物资,便挽起裤脚趟过浅浅的海水,把借着浮力把破碎的木板拖上了岸。
不对。阿尔弗雷德低头打量时神色一僵,木板的断裂面怎么可能这么整齐。他抽出随身带着的小刀向木板拼命扎去,只浅浅没入了刀尖。望着厚重木板近乎完美的切面,他不由得抖了一下。
该死。
海上常有诡谲的传说。用歌声魅惑水手的海妖,有着巨大腕足的黑影,吞噬一切的大漩涡……在海上谋生的人或许对上帝没那么虔诚,但一定对海神充满敬畏。广袤而深邃的未知足够令人恐惧。
阿尔弗雷德在炎炎烈日下,后背却出了一层冷汗。他在读书时的博物学成绩称不上优异,但足以让他意识到眼前的痕迹并非是世上任意一种已知的生物所能造成的,甚至任意一种已知的武器同样无法做到。
当天傍晚,名为王耀的男人又一次出现,自然而然地坐在营火边烤起了鱼,白日里阿尔弗雷德发现的残片就堆在一旁。王耀的目光扫过,停滞了一刹又淡然移开。
阿尔弗雷德这次不再偷偷跟踪,只是光明正大地坐到王耀身边,接过烤鱼时思索了一下,挑出一条最大的递给对方。王耀正扇着不知从哪儿来的扇子,见状“啪”的一合,虚着挡了一下,摇了摇头,眉眼间却染上一层笑意。
阿尔弗雷德见王耀拒绝,也不强求,只低头三下五除二解决了晚饭,随即厚着脸皮跟在了起身离开的王耀身后。王耀回头看了他一眼,有些莫名其妙,阿尔弗雷德讪笑着指了指海面,又指了指自己,期望着即使语言不通,王耀也能领会到自己想回家的意图。王耀沉沉地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阿尔弗雷德焦急地上前一步想开口,不知从何而起一阵狂风,卷起海滩上的沙子迷了他的眼。待他流着泪勉强睁开眼,已不见了王耀的踪影。
王耀没再来过。
不过烤好的鱼会随机出现在阿尔弗雷德身边,能活。
阿尔弗雷德有点郁闷。虽然流落荒岛不是王耀的错,但他这种定期喂食的行为总让他觉得自己是被圈养在了荒岛上的宠物。
//(潦草的一行)
我像是被囚禁在这座岛上了,不管走向什么方向,最后都会回到那个岸边。//
阿尔弗雷德走向海里。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磨损不堪,头发也暗淡干枯像是冬日的麦子。他太累了。他早已不再打理自己,不再寻找各种食物——反正王耀会送过来,不再想王耀的事情……他每天只是在这个比他家乡村落还小的小岛上奔走,奔走,然后一遍一遍看见自己放置在岸边的那堆船板的残骸出现在前方。
……我不信,我受不了了。
阿尔弗雷德走向海中,海水足够冰冷到麻木他的知觉,让他渐渐从噩梦般的现实中睡去,躲进安稳的黑暗。海水刺痛着他的眼眶,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一道硕大的黑影,以及反着暗金色冷光的,层层叠叠的鳞片。
再醒来时他在离家乡不远处的港口处被人发现,据说他死死抱着一块木板从海面上漂来,被渔民发现。阿尔弗雷德头痛欲裂,像是忘记了什么,比如衣兜里那片金属质感的暗金色鳞片的来历。
再后来他终于随着亚瑟的新船队抵达了东方,异乡人的衣着与语言都令他隐隐有些熟悉。有人看见他胸口用丝线穿起的鳞片,随即惊呼出声。翻译说那是龙鳞。
“龙?”阿尔弗雷德疑惑地看向他。龙是我们所崇拜的最强大的神兽,翻译解释道。“龙由蛟变化而来,蛟在修炼到一定程度是会出现心魔,被天道囚禁,唯有它们自己消除了心魔,天道才会解除禁制,允许它们化龙。”
翻译遥遥指向海面上一座极小的岛,说那便是化龙之所,自古以来唯一一条真龙便是从那座岛而生。“就在十几年前,蛟化龙,这座先前被隐藏起来的岛才得以被我们看见。”
阿尔弗雷德拿起望远镜,岛上的沙滩隐隐有一堆切割整齐的木板。
后记:
王耀是一条蛟龙,被所谓天道困在一座狭小的岛上,黑色的锁链说:
“你永远成不了龙。因为你放不下。”
王耀不知道自己放不下什么,他记挂着很多东西,比如中原的战火,比如百姓的哀痛。难道天道是因为他不会放下这些东西才囚禁他吗?这不合理。
他离不开那座岛,别人也进不来,日复一日,他先是忘记了外面世界的样子,又渐渐忘记了如何言语。毕竟在岛上也没人可以和他说话。他能感应到人的因果,那艘船上沾满了孽障,所以他用爪子悄悄把船侧划坏作为惩罚,离开时巨大的身体还被那艘船撞了一下。船上有个罪孽没那么重的年轻人,于是王耀乐得帮他一次,把他带回岛上。他还因这次擅自离岛遭了天谴,险些没维持住人形。本来维持人形就是麻烦事,只能趁着傍晚晨昏交接之时钻个天道的漏洞。
那年轻人有些过于自来熟,二话不说就和人肢体接触,不过,很温暖。海底很冷,王耀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这么温暖的东西了,也很久没有听过第二个人的声音了。王耀起了把阿尔弗雷德留在岛上和他作伴的念头,但这太卑劣了,他只好对自己说这是怕阿尔弗雷德有危险,毕竟这可是天道管辖的岛屿。可阿尔弗雷德还是要走,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孜孜不倦地在岛上寻觅,无奈之下王耀弄了个鬼打墙的小把戏,却未曾想阿尔弗雷德径直投了海。
王耀不想让阿尔弗雷德离开,可若强行留下他结果必然更糟。他还是放他走了。忍着身上锁链带来的剧痛,王耀离开了禁区,一直把阿尔弗雷德送到岸边。金色的血液一缕一缕飘散在海水中,王耀早已不觉得痛。临走前他还是担心阿尔弗雷德,便硬生生扯下了自己胸口的逆鳞给他,以便能和他维持或多或少的联系。反正鳞片还能长出来,他想。
扯下逆鳞那一瞬间很疼,他忍着疼痛往回游,本想着这下得被天雷劈惨了,没想到无事发生,等他回过神才发现,连身周的锁链也都不见了。
逆鳞是蛟龙一族的私欲,也是弱点。天道告诉他。“你放走了那个人,也放下了自己的私欲。拔下逆鳞的时候,你已经是龙了。龙和蛟唯一的区别,就是逆鳞。”王耀确实感觉自己产生了一点变化,低头时却赫然发现锁链再一次出现,只不过从黑色变成了金色。
“锁链囚的是你的心。”天道说,“只不过现在囚住你的不是天道了,而是你自己。”
王耀沉默地站了一会,一言不发地背对着海洋,向陆地深处走去,衣摆飘飘。
留下你想说的话:
一开始本来想写成克苏鲁风格的,但后来写的时候一直在想,“囚蛟”,王耀究竟会被什么囚住?我给出的答案是王耀自己。对阿尔弗雷德,对众生都有着放不下的执念的蛟龙耀,也许注定会从“小我”与“大我”之间作出选择吧。而最后王耀终于选择了“大我”,化成了龙,但我也不愿让他彻底撒手,所以选择了让他对阿米从“私欲”变为“牵挂”,毕竟是金钱组的文嘛(心虚)
总之艰难地写完了!没写出太明显的爱情不过写了一些自己对于情感的思考(?)以后我也要接着写金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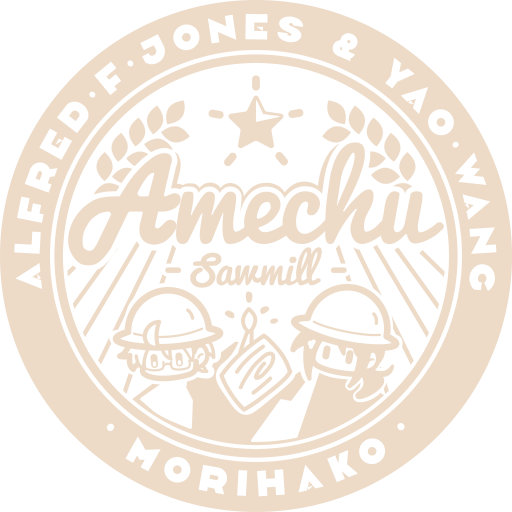
发表回复